|
|||||
 |
|||||
最新更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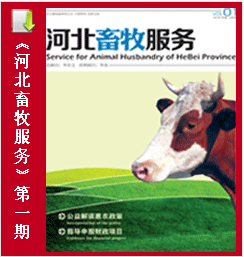
嘉兴“猪转型”:两年间90%生猪是如何消失的
新丰镇竹林村,原本“养猪明星户”的数千平方米猪舍所在地,成了林地和苗圃,他家也改行注册了园艺公司。孔令君 摄本报记者 孔令君两年前,也是这时节,乍暖还寒。传来黄浦江漂死猪的消息,数量很大,甚嚣尘上。
出这事之前,不少上海人还不清楚,自家吃的猪肉产自哪里;更不知道,在邻近的农村养上万头猪,会威胁到黄浦江,甚至饮用水安全。
矛头一致指向嘉兴,数百位记者蜂拥而去,把好几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。有蹲守一个星期的,看到了河道里的死猪,就像终于抓住了犯人似的:看!都是你的错!
长三角河浜细密成网,原因究竟是什么?
去年初,记者总想着没弄明白,就“偷偷摸摸”又去了一趟嘉兴,找了见过面的养猪大户。那时他家数千平方米的猪舍已拆了大半,养了20多年猪、一度被誉为“致富能手”的他,突然说不养猪了,要转养泥鳅和牛蛙。记者将信将疑。
后来记者又去过一趟,采访当地一位领导,谈与上海及长三角的关系。她感性,从城市发展讲到了“一只猪的启示”,谈及区域性、流域性问题的沟通机制,谈及生态环境的重要以及转型升级的难度。在座的人都感慨:“猪,是不能养了!”
最近记者还去,摸了几个已熟悉的养猪村,寻了故人。大不同!两年前曾经在十天内接受了上百家媒体采访的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,很有底气:村里已拆除违章猪舍38.7万平方米。
对!没听错。记者重复了好几次跟陈云华确认:确实,一个村子就拆了38万7千平方米的猪舍;而竹林村所在的新丰镇,生猪存栏量两年间减少了至少41万头,从45万头减少到了3.5万头。
看来,是时候谈谈猪的事了。
表面是一只猪,却可以剥皮深究,窥一眼整个长三角的转型升级的决心。
“嫌疑最大”的“死猪源头”
实际上,成百上千的猪漂到黄浦江,绝非“一日之功”。
但对竹林村来说,2013年的3月11日,事情搞大了。先是国内一家大电视台记者来了,扛着机器对着村里的猪舍猛拍一通,然后找到村支书陈云华,让他谈“猪的事”。
那一天,陈云华当上村支书才4天,在镜头对准他之前,他还不知道发生在黄浦江的事。压力之下,他满脸涨得通红。
紧接着的十多天里,全国各地涌来了数百位记者,有自己“摸”来的,也有经过当地政府安排,一整批坐车来“要求参观”的。
记者当然知道竹林村突然火爆的原因—就在几天前,当地报纸刚做过系列报道,有读者反映,有记者暗访,并提出“死猪处理”,是“一个养殖大村之痛”,稿件中写道:“被丢弃的病死猪,有的装在化肥袋子里,有的直接暴露在河岸上,不少死猪身上已经长出了青苔……”
这些稿件,篇篇指向竹林村。
这个村子,是当时记者们在网络上能搜索到的,唯一的、也是“嫌疑最大”的“死猪源头”。
在长三角地区,嘉兴原本就是“养猪大户”,而最出名的就是“新三桥”,分别是新丰、西塘桥、凤桥、曹桥,这4个乡镇在地图上基本形成一个三角形,被称为“猪三角”。而即便是在“猪三角”中,竹林村也是“大户”。
毕竟拆了38.7万平方米,想想当年盛况,也是醉了。
两年前记者在村间小道上和陈云华无意中狭路相逢时,他背后拥着一大波记者,要带他们去看一处病死猪处理池。那里的水泥盖紧紧盖着,打不开,实际上也没人真正想把它打开。盖子旁边的化肥袋里,露出一只刚死不久的小猪。于是相机咔咔咔,响个不停。
陈云华还推荐大家去看村里建的猪废物收集处理中心。而人们不管看了没看,还围着他要生猪存栏量,要病死猪率,看到猪舍门前散落着抗生素药罐,又缠着问猪肉安全问题;还有各路插进来的记者,要求解答猪耳标的问题;还有外国媒体,雇了地陪和翻译,一个劲地问沼气池建得够不够。他能回答的,都回答了。
那十多天里,他每天都在接待记者,每天大早上出门,晚上10时前绝对回不了家。到家后,别提看电视、关注舆情啥的,倒头就睡。
其中有一天,他跟村里的老书记讲:我这个书记估计当不成了,才上岗就要下岗了。
“猪实在太多了”!
陈云华也是自信的,被媒体轰炸了好几天之后,有一天再次面对大电视台的镜头,他坐正之后,抖了抖西装领子,微微一笑问旁人:我这样还不错吧。
毕竟,竹林村“猪多业大”,各方面配套做得也齐全,镇干部、村干部每年70%的工作,都用在猪上,检查、统计、防疫、整改……对于环境的压力,他们也早意识到了,不断要求养猪大户“两分离三配套”,这是不少嘉兴村镇干部非常熟悉的词,即“雨污分离、干湿分离;沼气池、沼液池、干粪堆积池配套”。
扔死猪的,村里也抓,白天里河道里捞出死猪,肯定按耳标查,追到了逃不掉罚款几百元,很严的。
而早在2011年,嘉兴市政府就出台过《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。
不是没在做,而是“猪实在太多了”!
当地镇里分管招商的干部和记者开玩笑说,以前客商来,不用看路牌,只要摇下车窗,闻到猪臭味越来越重,就知道快到了。记者两年前来,几个村房前屋后都是扩建围墙和小棚子,养猪用的。
干嘛不养啊,太方便了。农村老人养上十来头猪,一天喂食两三次花不了多少时间,田活不耽误,带孙辈也来得及;买饲料、打防疫针、卖猪一个电话都能上门。在长三角不少地方,养猪原本就是习以为常的副业,一户普通人家一年“顺便”养一些猪,赚得少有一两千元,赚得多有一两万元。对广大“散户”而言,成本只是自己劳力及一些米糠油糠,照农村观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。
至于环境污染嘛,在轻松创收面前,似乎并不感觉得到。当年就有养猪户坦言,一直在这生活不觉得臭,只有偶尔从镇上回来,才会突然发现,猪哪能这么臭!有些断头的死河浜,淤积了太多猪粪和垃圾,河面成了腐臭不堪的陆地,常看到鸡鸭鹅,摇摇摆摆走过河去。
这位养猪户也想不起来,啥时候变成这个样子,老早之前,自己就在这河里游泳钓鱼来着。
两年后的原因分析
在大批死猪漂到黄浦江之前,在很多人看来,臭河浜之类不算啥大事。
但漂猪新闻一出,嘉兴不少干部忙坏了,每天一起床就往村镇赶。省里市里大动员,要求深入开展清查,“不失时机,不留死角”。河道里多了不少船,拉网式打捞、处理河道漂浮物;田间地头、农村房屋前后都被要求清理。
很多人追着问,到底是什么原因,导致大量死猪漂到黄浦江上?并补上一句,以前为啥没有?
当时看不清、讲不清的,两年过去,更清楚一些了—一、死猪扔河浜,以前也有,从长三角地区农村普遍养猪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; 只是量不多而已。
三、曾经还有过死猪不扔河浜,是因为能卖出点钱,有人非法收去屠宰加工成猪肉,卖到工地食堂小吃店; 当时嘉兴严抓严打,2012年当地法院刚判了一个制销死猪的大案,一个团伙均被判重刑,其中3人“无期徒刑”,村里没人敢收死猪了。
四、理论上,各乡镇对处理病死猪均有补贴,发给上门收猪人和养猪户,每头少则十几二十元,多则八九十元,但各村执行千差万别,有资金不到位的,也有干脆不发的。发与不发,直接关系到死猪扔或不扔河浜里。
五、2013春节前后,忽冷忽热温差大,病死猪尤其小猪数量增多。记者的这一判断,来自平湖市广陈镇龙兴村的养猪大户马保良,他家猪舍条件很好,铺地板、有“小太阳”供暖,可那时节也挡不住。
市里下了大决心
暂不说典型的竹林村,找个偏僻一点的普通村子—平湖市曹桥街道的野马村,两年前数百位记者拥入嘉兴,也找不到它这儿来。这是个纯农业村,村子距离主干道远,若种植大棚蔬菜啥的,卖出去不方便,村里世世代代,养猪都是条好路子。
村支书王亚勤,风风火火的女同志,她仔细回想,从2007年开始,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到猪上,每天都督促着养猪户“两分离三配套”,忙着发告知书和宣传材料。环境不好了,她也着急,小时候游泳洗衣服的小河,早已经臭得不成样子。
可她从没想过,养猪这件事还可以“大逆转”啊?
在“黄浦江漂死猪”的舆论风波平静之后,没过多久,她被通知去嘉兴市里参加关于养猪“千人大会”,还要求她表态发言,当了十多年村干部,可从来没到市里开过会。
市里下决心了!猪是不能再多下去了!正逢浙江全省范围的“三改一拆”和“五水共治”,嘉兴下了大工夫,拆除违章猪舍、治理水环境,进而转型升级。
嘉兴市委书记鲁俊曾和记者开玩笑,说那段时间自己是位“猪司令”:为了拆除违章猪舍,她光是新丰镇就去看了5次,现场开座谈会,第一次动员不养猪;第二次动员拆猪棚;第三次做“钉子户”的思想工作;第四次要求对确有困难的养猪户帮扶到位;第五次,她请村镇干部们吃年夜饭,为了猪的事,辛苦了!
工作都是村干部带头的。
王亚勤做的第一件事,是跑到娘家去,哄着老母亲和弟弟,把家里猪卖了,把后院200平方米的猪棚拆了。老妈不愿意,说不养猪就没事干了,还说就养两头有啥呢,又不养多。王亚勤先劝弟弟再劝娘:拆了吧,否则村支书工作不好做。
如今,她家弟弟、弟媳都在服装厂上班,每天都接了点活回家,给老妈缝缝纽扣啥的,赚点外快。如今她母亲乐得很,说“没那一身臭味道”了。
陈云华呢,他也是村里不大不小的养猪户,家里也建有1000多平方米的猪舍。先从自己下刀,卖猪拆猪舍。收猪的经纪人知道他是村支书,有决心,卖得又急,所以价格上不去。如今呢,陈云华带头在村里种植生姜,这几年行情还不错。
原本想都不敢想的“猪转型”
想法也不是一下子转过来的。有村干部坦言,刚开始时候一两个月,一户都拆不下来。
养猪户们曾把矛头都指向村干部。拆违章猪舍第一年间,陈云华去找老书记“求开解”。老书记说,拆违章猪舍从长远来说是好事,村里现在怪你,但过几年就好了,子孙后代肯定说你好。
陈云华又跟老书记说,我估计这次村里选举,我选不上了。老书记说,你看着吧。
后来,陈云华全票当选村支书。
再后来,有因为不让养猪而闹过矛盾的村民主动找上陈云华,尴尬地打哈哈,说讲老实话,如今心里是服气的,整片的猪舍变成了菜园,大片黄绿,舒心得很。这几年猪价也“配合”,跌跌不休,不少养猪户亏了,可家里有猪棚,骑虎难下,还有来村委会求着拆违章猪舍的。
王亚勤那边,靠的是她“铁娘子”的苦口婆心,每户人家她都上门走访10次以上,讲退养补贴政策,讲环境,说以前村里多好啊,河里游泳洗衣服,现在搞得洗拖把都嫌脏……如今的野马村,猪从3万多头减至不到2千头,“回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”;竹林村呢,猪少了之后,村里突然有了新乐子—女人跳舞!每天晚上村里的小广场,小音箱一响就爆满,大妈大姐都来跳舞,还成立了舞蹈队。男人钓鱼!似乎是发现新大陆一般,村里不少人发现河浜里有鱼了,“虽然远不及小时候,但两小时下来,也能钓上七八条。”周凌峰说,环境大变样,也就一年半时间,他也觉得神奇。
周家是竹林村的“养猪明星”,周凌峰的母亲胡玉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养猪,曾因为猪养得好、带领村里养猪致富,还获得过浙江省“三八红旗手”,其它各种荣誉多了去了。他们家也曾是竹林村最大的养猪户,猪舍面积达到近4000平方米。
如今呢?原来的猪舍成了林地和苗圃:林子里养了贵妃鸡;靠近主干道的一侧,建了玻璃房子,成了苗木花卉的展示中心。因为附近河里能钓鱼了,周凌峰还计划开农家乐,供城里人钓鱼喝茶聊天。目前这样一年下来,一家人有20多万元的收入,和养猪时相比收入减少,但风险也小了。
大户大转型,小户也改行。竹林村搞了好几期技能培训班,有教授大棚种植的,也有对口临近的工厂岗位,教技术的;还有针对妇女,安排家政服务工作的。在王亚勤的牵线搭桥下,野马村村民从镇上的服装厂接了单子;村镇工厂开招聘会,也优先招录生猪退养户,并放宽年龄限制,村子里的施工、河道保洁都能优先安排;而村里60岁以上的生猪退养户,每人每月有100元生活补助,再到村里合作社的菜地打打工,每年能到手的钱,和养猪差不多。
让陈云华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,相比臭烘烘的大养猪时代,他突然发现如今村民对环境要求高了很多—村里企业的烟囱一冒烟,就有人到村委会举报,说人家“乱排放”!看到别家在河岸上丢放垃圾,竟冒出好几人追着要说法,闹到村委会,倒说要“监督环境”来了。
这一切一切,两年前,谁都不敢想!
记者手记
猪和烟囱,是消失还是转移了?
嘉兴“猪转型”的背后,是整个长三角在经历粗放式发展后,全社会的主动自我反思。未来长三角的发展,必定是更加牢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更追求人们的终极幸福。
这片土地上原本数百万头猪,能在两年间消失到只剩80多万头,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却也做成了。就像原本长三角林立的烟囱和排污管,如今大多数也消失了,生活质量却不降反升。大家回过神来,个个点赞叫好。
可记者放不下心的,在于这些猪和烟囱,究竟是消失了,还是转移了。
目前打听到的,是嘉兴的养猪大户,有被中西部省份重金请去,担任“技术顾问”的。电话打去一问,说那边养猪,基本还是老早的“嘉兴模式”,整个村子都是猪臭味……长三角在自我反思,转型升级、创新发展,而这些反思后的成果和经验,能否早一些复制推广到更广大的地方去。毕竟,这片天空和空气,这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,都是我们共有的。
本站原创文章,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于河北畜牧服务网。 行业资讯录入:本站编辑 责任编辑:管理员
相关文章:
河北畜牧服务网版权所有@2011-2016 冀ICP备12002456号
联系电话:0311-67303882,67303883, 18633000595 传真:0311-67303883
在线咨询QQ:
 信息员网群:225696333
信息员网群:225696333
网站地址: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维多利亚时代12号楼1单元201室(地图)
[本站声明] 本网站为服务河北省畜牧企业的公益性网站,因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来电告知,本站将立即更正。
联系电话:0311-67303882,67303883, 18633000595 传真:0311-67303883
在线咨询QQ:
网站地址: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维多利亚时代12号楼1单元201室(地图)
[本站声明] 本网站为服务河北省畜牧企业的公益性网站,因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请来电告知,本站将立即更正。



